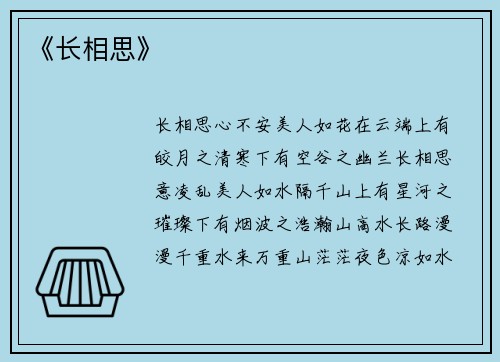「名家专栏」冯积短篇小说《母与子》



母与子
文/冯积岐
躺椅是母亲搬上街道的。母亲双手抓着躺椅两边的木框,手的颜色和木头的颜色几乎是一样的沉静一样的黯淡,手似乎比木头更粗糙些。母亲的手已是青筋毕露了,不过,那也是她用力气的结果,母亲全身的力气全都集中到手上来了——那把躺椅在母亲的手中份量并不很重。母亲将躺椅展开在街道上的树荫下。天气很热。狭窄的街道粮食口袋似的把暑气全装在里面了。树荫虽然极其有限,人躺在树下,心里就有了点凉意,那是树的叶片儿偶尔地摆动带来的,尽管只是微弱地摆动。搁好躺椅,母亲伸直了腰,她掠了掠头发,头发中的白丝比她脸上的皱纹还要多。母亲抬起了明晰而坚定的目光:街道的南端,有一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在太阳地里艰难地行走,车轮子很涩滞。当时,母亲就想给儿子买一辆轮椅的,钱也凑得差不多了。可是,儿子坚持不叫母亲买。儿子的想法是对的,轮椅无法对付乡村土路,道路凹凸不平,儿子受不了那种颠晃。她和儿子都还有一丝渺茫的希望,希望脊柱神经能够弥合。轮椅终究没有买。车轮子从母亲的视线里逸出去了。拉车人到了母亲跟前。拉车人是用碗碟换粮食的小贩。母亲将支好的躺椅挪了挪,让拉车人同架子车一起挤到了树荫下。
母亲背着儿子走出了院门。儿子的双手从母亲的肩上搭过去,趴在母亲的背上。母亲的腰弯下去,步子很稳。儿子的目光垂下来,不曾从母亲的头发上越过去,他只是看着母亲的后颈和肩胛,母亲肩胛上的骨头清晰可辨,这些历经了六十个春秋的骨头,这些已经开始变轻的骨头,这些只是紧紧相连,用来结构人体的骨头,是怎么样支撑着母亲的,是怎么样背负着儿子的,只有儿子知道,深入到骨髓里面的是母亲的精神,是母亲的情感,失去了这些,母亲的骨头就会毫无力量,就会散了架。趴在母亲背上的儿子只是皱眉头,只是咬牙齿,这是他宣泄情感的最简单最朴素最忠诚的方式——他已经流不出眼泪来了,哭不出声音来了。母亲的骨头准确无误地传递着儿子此时的心情,儿子最细微的情感变化也在母亲的感觉中。母亲叫了一声:“来来。”儿子垂下的目光抬起来了,他看见了灼人的太阳光,看见了那张躺椅。
连续生过四个女孩儿之后,母亲有了抱养儿子的想法,她太想有一个儿子了。儿子是从月子里就抱养来的。儿子满月那天,母亲给他起了个名字——来来。母亲将儿子的名字和她的四个女儿紧紧相连(来霞、来芳、来娟、来惠),是为了表示,儿子是她亲生的。儿子在母亲的眼睛里长大了。初中毕业后,儿子坚持要学手艺,母亲就随了他的心愿,让他跟着村里一个既精通木匠活儿又擅长瓦工的人学手艺。儿子一点就透,十八岁就出师了。儿子的有出息安慰了母亲,母亲打算将几间旧厦房拆了,盖一座大瓦房,然后,就给儿子结婚。正当母亲兴致勃勃地勾勒着未来的蓝图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儿子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那一年,儿子二十岁。花完了家中的所有积蓄,卖了猪和羊,卖了耕牛,跑遍了省内外十几家医院,也未能使儿子站立起来。他瘫痪了。母亲的脊背负载着儿子的愿望——不仅仅能够使儿子目睹屋外的世界。
母亲将儿子放在了躺椅上。
母亲的脊背上被汗水濡湿了一大片。她撩起衣角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母亲和儿子的目光相遇了。母亲给儿子撒下了一大片疼爱、呵护的目光,她一句话也没说,回到院子里去了。
“咋成这样子了?”小贩扫了躺椅一眼。“摔伤的。”他说。
“有好几年了吧?”
“十年了。”
“那是你妈?”
“当然是我妈。
小贩叹息了一声。
“有啥唉声叹气的?得是愁碗碟换不出去?”母亲拿着一把扇子出来了。“喝水不?”
“不。”小贩尴尬地摇摇头:“前边那个村子叫啥村子?”
“杜村。”母亲说。“有碗碟就能换来粮食。”
“我要去杜村找一个人。”
新利Lucky小贩大概不敢面对这母子俩,他拉着架子车走进了太阳地里。
“妈,我想……”
儿子把手里的扇子摇了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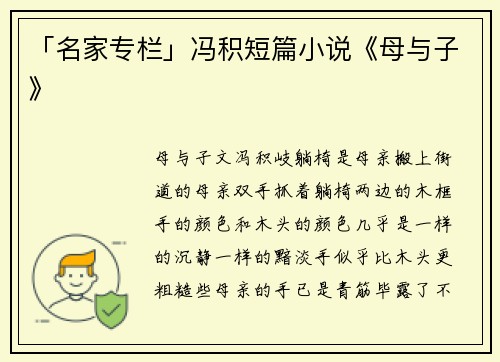
“得是想拧绳子?”母亲说,“这么热的天,算了吧。”
儿子朝母亲的脊背扇风。
儿子那双拿斧子拿锯子拿瓦刀的手变了,变得很灵巧、很细致,他学会了拧绳子,学会了纳鞋底,学会了上鞋帮。除此之外,这双手还能干什么呢?儿子知道,他将永远也站不起来了。他想,他用一双手可以减轻母亲一些负担。可是,他不可能每天都干那些活儿的,他绝望了。他对付自己的第一个办法就是绝食。任凭母亲劝慰开导,任凭母亲啜泣流泪,他不动筷子,甚至连一口水也不喝。儿子的心上好像堵了一块黑色的岩石,再有力的语言也吹不进去了。于是,母亲就陪着儿子绝食。儿子宁肯自己死去,也不愿意伤及母亲。儿子端起了饭碗,他吃一口,给母亲喂一口。当母亲将他背出院门,又背出房间的时候,儿子哭了:他被母亲背到什么时候才会到头呢?听见母亲的脚步声还在院子里,儿子就从炕上扑下去了,他摔得皮青面肿,他不愿意母亲再背他。他不想再连累母亲了,母亲为了他,几年间白了头发弯了腰。他又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趁母亲在灶房里做饭的时候,解下裤带,拴在了窗框子上,将脖颈套进去,想把自己勒死。母亲进来时,他已窒息了。母亲解救了他。母子俩抱头大哭。就在那一天,他给母亲发了誓,要好好地活下去,好好地做人。是母亲提出要他学画画儿的,母亲不指望儿子能画出什么来,只是希望他手不闲。他从那天起,开始学画画儿。
母亲像伺候婴儿一样伺候她的儿子,儿子大小便失控了,每天要母亲接屎接尿,母亲常常累得满头大汗。婶婶看着母亲受作煎,就将她叫去对她说,你还有来虎呢(抱养他的第三年,母亲生了一个儿子),来虎可以顶门立户了,你就叫来来去吧,他这样活着也是活受罪。母亲一听,对婶婶怒目而视,她顺手掂起案板上的切菜刀说:“你去把你儿子的手指头剁一根下来给我看看。”婶婶吓得再也不敢吭声了。
现在,母亲坐在儿子的躺椅旁边。母亲要给儿子扇凉,儿子要给母亲扇凉。后来,扇子还是到了儿子手里,他给母亲扇。
“妈不热。”母亲说。
“还不热?”
“心静自然凉。”母亲说,“入伏入冷哩,伏天儿一满,天就凉下来了。”
“伏天也快满了。”
“是呀,”母亲说,“天凉快了,妈准备给你弟弟结婚呢。”
儿子手里的扇子掉在了地下。母亲抬头望着远方。儿子拾起扇子说:“来虎也该结婚了。”
来了一缕风。风是从树的枝叶间筛下来的。
“好凉快呀。”儿子说。
“天上有云了。”母亲说。
几团乌云眨眼间从四面八方拢过来了,拢在了太阳四周。太阳在云朵中徐徐缓缓地穿行。“妈,我想画画。”
“现在?”
“现在。”儿子说,“给你再画一张像吧。”
“那好呀!”
母亲给儿子取来了画板和铅笔。
母亲将头发又拢了拢。她坐得离儿子的躺椅稍远一些。
儿子开始给母亲画像。
母亲枯瘦的双手搭在了双膝上,她的腰板尽量地挺直,眼睛看着街道南端:街道很不平整,好像一张跷跷板在太阳地里晃动着。又是一阵凉风,风将母亲的白布衫翻卷了,母亲的白发在风中飘动。儿子注视着母亲的脸庞,母亲的神态使他感动。儿子不知道给母亲画过多少张像了,每画一张,母亲都要高兴半天。尽管他画得并不好,而母亲凝视着画像总是要说:“妈有这么年轻吗?”“妈有这么刚强吗?”“妈有这么好看吗?”儿子说:“有,有。”
母亲拉了拉衣襟说:“你要把妈画成六十岁的样子,妈今年整六十了。”
儿子说:“妈,你放心。”儿子注视着母亲,他的目光很少在画板上,只听见铅笔在画板上擦出来的极其微小的声音。
街道上有了太阳的阴影。太阳的阴影在母亲和儿子的身后边。
清早起来,母亲给儿子拿来了剃须刀。儿子对着镜子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的。母亲今天要给她的二儿子举办婚礼。母亲忙坏了。刚开了席,母亲就给儿子端来了面条,照顾着儿子吃了早饭。儿子问母亲,有他干的什么活儿没有。母亲说没有。母亲知道儿子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儿子不瘫痪,儿子也是有了儿子的人了。可是,这一辈子,他是和结婚无缘了。
母亲说:“今天家里客人多,乱糟糟的,妈给你从外面把门锁上,省得有人来骚扰你。”
儿子说:“妈愿意锁就锁。”
母亲说:“晌午开席前,妈就给你把饭端来了。你躺不住,就画你的画儿去。”
儿子说:“妈你去照顾客人,不用管我了。”母亲从房间里出来后,给儿子锁上了门。后来,母亲感到应该自责的是,不该给儿子锁门的。当时,母亲为什么要上锁,她大概是有她自己的想法的,儿子也大概觉察出来了,就爽快地答应了母亲。
儿子躺在坑上,不错眼地看着席棚,顶棚上的席子发黄了,雪白雪白的席子十年间变了颜色,席子上的“人”字形花形像燕子似的在飞,飞得满屋子里都是。其实,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儿子自己能听见自己呼吸和心跳的声音。他不再看席棚了。他从枕头旁边拿起了夏天里给母亲画的像,儿子端详着画面上的母亲,他将母亲的画像捂在胸口上,沉思了一会儿,又开始用铅笔修改。他一边修改,一边回忆母亲当时的神情。他第一次觉得,手中的铅笔好像不听使唤了,越修改,越不能随他的心愿了。
热烈的鞭炮声从院门外一路洒进来,洒到了院子里。院子里的气氛似乎和儿子无关,他给母亲的画像补了最后一笔。 铅笔在他的手中出了汗。他的手指头像铁钳子一样把铅笔紧紧地钳住了,他的左手使劲扳,才扳动了右手的手指头。铅笔落下来了。儿子活动了一下紧张的手。他回头一看,目光透过窗子上的那块小玻璃可以看见秋风在后院里的白杨树上高兴着,一片绿叶正在顺风而下。儿子用一张画纸堵在了那一小块玻璃上,他闭上了眼睛,休息了一会儿。
新娘在鞭炮声中进了门。她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儿?儿子睁开了眼,席棚上的“人”字又在乱飞。他的手在炕上一摸,摸到了清早起来刮胡子时用过的大方镜子。她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儿?个子高高的,脸庞上白处白,红处红,脖颈特别洁净,眸子尤其黑,像雍山里的黑水潭那么亮。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那一刹那间似乎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儿,她大呼小叫地朝他跑来了,她大概伸出双臂要接住从高处摔下来的他,不让他扑向地面,她在他的视线里只是一旋转,就消失了。他看见的不是那女孩的脸,而是自己的脸,在镜子里。他的目光渐渐地平静了。他端起了画板,开始给自己画像,他画得很艰难,在镜子里照一会儿,在画板上抹几笔。
婚礼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房间里沉静如铁。儿子的铅笔在画板上画出来的声音仿佛犁铧在土地上耕耘,儿子画得额头上出了汗。他似乎连自己也不相信,画纸上画出来的就是他!他给手上再一次使劲,“咔嚓”一声,铅笔断成了两截,席棚上的“人”确实震飞了……
晌午饭要开席了。母亲左手端着多半碗肉和菜,右手拿着两个白面馍馍,走到了儿子的房门口,母亲将馍馍放在了菜碗上,右手用钥匙去开门。母亲开门的手在颤动。她打了三次,才打开了锁。她从来没有这样过,即使闭上眼睛也能打开那把锁的。母亲的手臂一抖动,心跳也加快了。推开了房子门,母亲将菜碗放在了柜子上。她以为儿子是睡着了,连叫了两声,儿子没有吭声。母亲心里的声音明朗了:儿子不是睡着了。她撩起被子一看,儿子用剃须刀将手腕上的静脉割断了,血似乎还是热的,热的血在炕上爬动着,艰难地爬动,穿过了儿子的身体,爬到了母亲的跟前。母亲看了看儿子平静的脸,在心里说,妈是老糊涂了,你不会抱怨妈吧?她似乎听见儿子说,不会的。母亲关上了房间的门。她将儿子身上的血揩干净,从柜子里取出来一身新衣服,给已经僵硬的儿子穿在了身上。母亲看了看儿子,给他盖上了被子。这时候,她才发觉了儿子的自画像。她将儿子的自画像仔细看了看,纸上的画像一点儿也不像儿子。母亲将画像立在了柜子上,那个菜碗就祭献在画像前。
母亲做完了这一切,很平静地走出了房间,重新锁上了门。
晌午饭在一串鞭炮声中开了席。
热闹的气氛像正午的太阳一样在院子里照耀。
母亲走到了后院里。站在那棵白杨树下,背对着院子里的热闹,她潸然泪下了,一片绿叶擦着母亲的肩头落在了地上,母亲以为谁推了她一把,她匆忙擦干了泪水。低头一看,她的脚下原来是一片绿叶。
院子里,有人在喊叫:“来虎他妈呢?”
母亲欣然答道:“来了。我来了。”
原载1998年《北方文学》10期